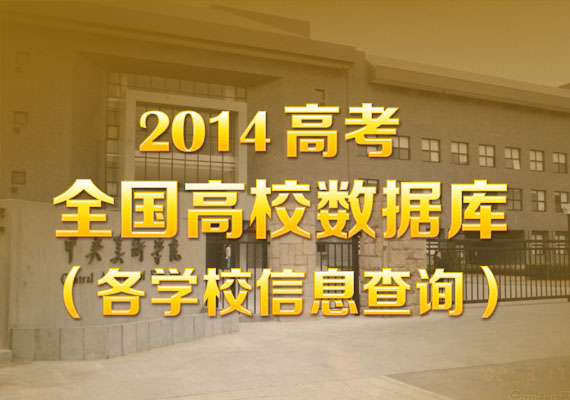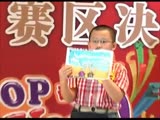当然,学习并不仅限于听课。子曰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改之。”三人行尚且如此,何况我们近乎三十人行。贺庆荣老师旅居英国多年,和我们在一起不忘时不时传授些诸如spitting、chav、lager之类英伦特色词汇,也在伦敦做了我们半个导游,我们常常佩服其知识渊博,更是被其在如此渊博情况下依然孜孜以求的精神所震撼。
当然,学习也不仅限于教学方面。单一化的饮食随时挑战着我们对英伦文化的接受和认可,于是乎,老干妈、榨菜、泡面、海带丝都成为了桌面上的珍品,而颇有远见携带这些漂洋过海的老师们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豪,因为大家都愿意和他们交朋友。我始终保守地信奉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.,这是我幼时在美国学会的重要的生存之道,所以我拒绝了土豪们慷慨的offer,坚持live in Britain as a British(虽然用“坚持”并不合适,因为英国的食物就和它的天气一样,虽然远谈不上agreeable,但至少acceptable)。在大家疯狂血拼时,我更多地选择了慢节奏的life enjoyment模式:时而走街串巷,时而停下脚步来杯英式下午茶,时而走进各种琳琅满目的小商店跟店主相视微笑来句hello,时而从高处远眺整个城市,时不时通过深呼吸来赞美空气的清新,白天沐浴阳光之下,夜晚行走于人烟稀少的小道上与路灯相伴,这些或许就是我的游学模式。这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,也不存在所谓正确的方式,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,但这些更让我接近local style,没有什么比住在当地、跟当地人一样生活上几周更让我觉得惬意了。
于是乎,贺老师跟我们聊的属于language shock,培训讲座属于academic shock,饮食则代表了culture shock。Dr. Karen Ottewell所描述的外国学生在英国学习遇到的三种shock在我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个人旅行缺少了language awareness,会遇到一些语言问题,但无伤大雅时不会刻意关注;没有一个像贺老师这样通晓该L2(second language),又能用我们的L1(first language)来进行讲解的人,或许交流时潜移默化地习得一些(implicit learning),但我们又缺少了explicit learning;由于个人旅行很少会在一个地方像当地人一样住上一周以上,所以culture shock也体验得不够充分;当然,如果没有培训学习环节,自然更谈不上academic shock了。这便是我们这次游学与短期旅行的最大区别。
“吃”在牛剑
至此,大家或许很感兴趣,我们的味蕾是如何被虐的。虽然相对”学“而言,”吃“完全不是本次游学的主题。但为了缓解大家读完”学“之后的枯燥感,”吃“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,引用Dr. Linda Fisher的一句话来说就是:“You try not to put too much irrelevant information in your teaching. But if say it helps the student to focus, then you have a perfect reason to leave it there, as long as it's not too much.”

其实,英伦的食物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令人作呕,只不过每天重复一样的“美食”比较dull而已。所以“美食”虐我千百遍,我待美食如初恋,因为我坚信“美”不在于景,而在于你有一双善于发现“美”的眼睛。所以体验不同的变化就是我定义其acceptable的主要原因。而变化不是指各国美食间的切换,而是指各种英伦美食间的切换,当然,偶尔下下各国餐馆也未尝不可,因为这也是当地人的选择之一,何况各国美食到了英国,或多或少会被本土化一些,也算是值得尝试的新品种。